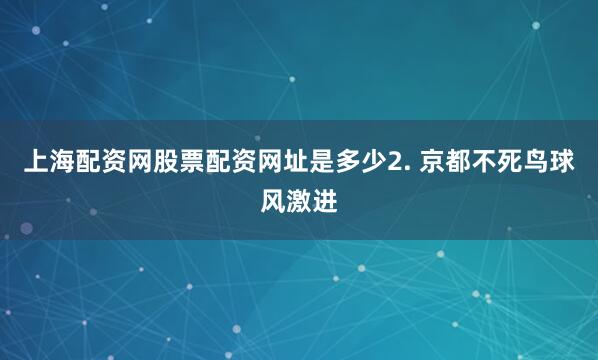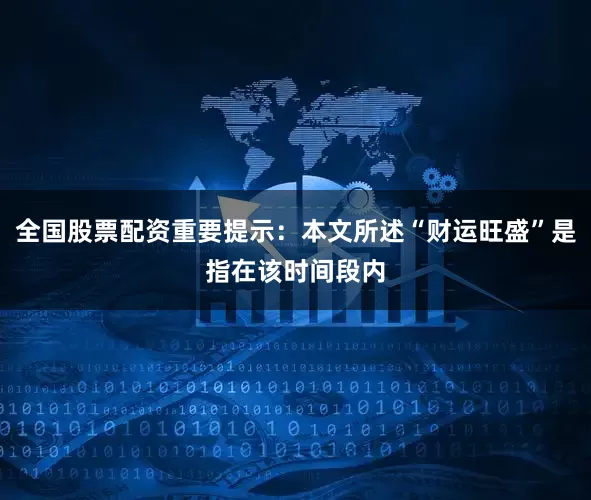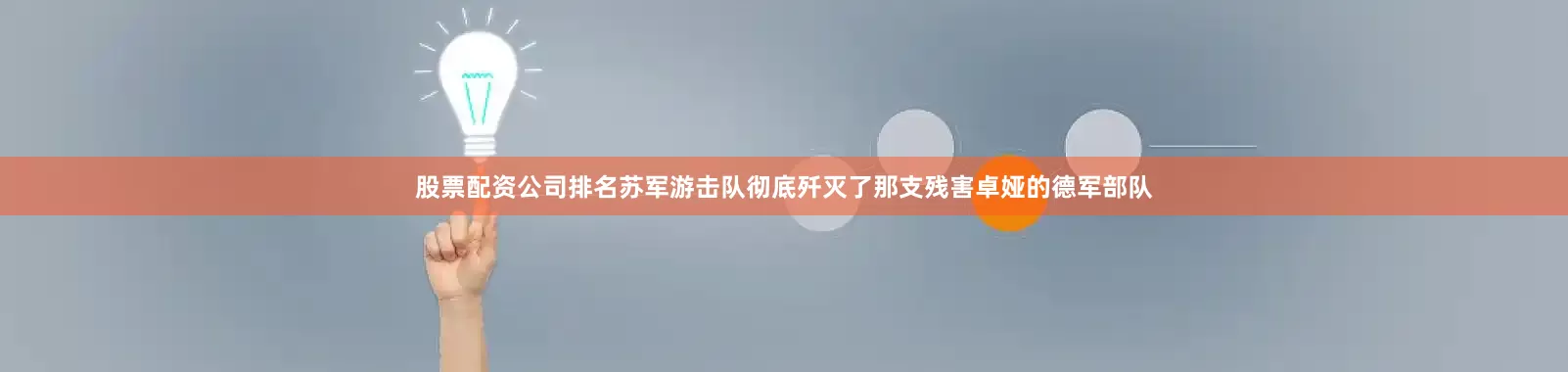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的战争,随之产生的战俘数量也创下了历史之最。各交战国为安置大量俘虏,纷纷建立了众多战俘营。这些战俘营的条件差异极大:有些极其恶劣,甚至残忍至极,如德国和日本;有些则相对人道,比如轴心国阵营中较为特殊的意大利以及法国;还有部分国家则要求战俘从事劳务工作,典型例子是美国和英国。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俘营,苏联对不同国家的战俘有区别对待,尤其对日本战俘待遇尤为严苛;而我国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对战俘的待遇则显得尤为宽厚和人道。
在二战期间,各国对待战俘的态度和政策各不相同。轴心国中的德国和日本,以残忍折磨战俘闻名,美英苏等国则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措施。若说残酷无情,二战日军对战俘的虐待位居第二,几乎无人敢称第一。日军将大量中国战俘送入人体实验室,进行令人发指的反人类医学试验,而面对美军战俘同样毫不手软。
展开剩余88%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军在巴丹半岛惨败,被迫向日军投降,数万美军战俘遭遇极端折磨。日军强迫这些战俘在饥饿疲惫的状态下,步行五天穿越一百二十公里,途中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只要有人倒下就被当场枪决。沿途,菲律宾当地民众同情美军战俘,偷偷投掷粮食和水,但这些善意全被日军阻拦,更有甚者,日军会殴打甚至枪杀帮助战俘的平民。
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跋涉后,美军战俘终于被押往巴丹战俘营,但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残酷的非人待遇。在这里,美军战俘成为了日军射击练习的靶子和刺刀试验的人肉沙袋。日本军官们时常因一时兴起,将数名美军战俘枪决或砍头,作为娱乐。炙热的巴丹半岛阳光下,战俘们还被迫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许多人因脱水而死。
除了巴丹战俘营,1943年日军在中国沈阳还设立了一个大型盟军战俘集中营,专门关押美英战俘,并在营内进行极其残忍的人体实验。日军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调来大批科研人员,将美英战俘当作试验对象,注射细菌以观察病变反应。实验内容包括冻伤、灼伤、换血、毒气暴露等各种恶性试验,甚至故意制造鼠疫以采集数据。
日军对战俘的残酷变态令人发指,而紧随其后的,便是同属轴心国阵营的纳粹德国。德军的战俘集中营,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欧洲乃至全球都声名狼藉。除大量犹太人外,这里还关押了众多战俘,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纳粹德军在将战俘送入集中营前,会先核查身份。犹太人或共产党员立即被处决,其余战俘则在惨无人道的生活中挣扎。德军常常对战俘施以殴打、电击,任何反抗行为都可能被关进毒气室,遭活活毒死。
巴丹和沈阳战俘营中战俘的死伤比例超过一半,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更为骇人,活着离开的战俘不足十分之一。除奥斯维辛外,其他德军战俘营对待俘虏同样残酷,苏联女英雄卓娅的悲惨遭遇便是明证。
1941年,年仅十八岁的苏军女战士卓娅被德军俘虏。为了从她口中获取情报,德军施以惨无人道的折磨。寒冬时节,德军剥光她的衣服,让她赤身站立在冰冷刺骨的雪地里;用沾盐水的鞭子抽打她的身体,甚至组织多人对她施暴。卓娅在极端折磨中坚贞不屈,最终被德军用刺刀活活杀害。她的悲惨遭遇激起了苏联上下的愤怒,激发了苏军的战斗热情。随后,苏军游击队彻底歼灭了那支残害卓娅的德军部队,为她报仇雪恨。
除了亲自折磨战俘,德军还在一些大型战俘营里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诱导一些意志薄弱的战俘成为纳粹的帮凶。这些人或被胁迫,或被利诱,虽身为俘虏,却残忍折磨自己的同胞,导致许多战俘失去反抗勇气,选择自杀。
与德日的残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轴心国的意大利在战俘管理上表现得较为宽厚。被意大利俘虏的美英士兵回忆,意大利战俘营普遍保障基本的生活和饮食,有些营地的伙食甚至优于英军前线士兵。意军还积极开展换俘行动,许多盟军战俘得以重返战场。未被换俘的战俘大多也平安回国。意大利采取宽容政策,部分源于国内激烈的反战思潮及军队内部强烈的厌战情绪。二战后期,意大利游击队更是推翻了墨索里尼纳粹政权。
意大利宽厚的态度也获得了盟军的相应回报。盟军对待意大利战俘通常较为宽容,鲜有虐待行为。与意大利类似,“自由法国”领导的法军也保持了较好的人道标准。尽管法国政府早早投降,但“自由法国”持续抵抗到战争结束,俘获了大量敌军。
法军的战俘营基本保障衣食,并尊重俘虏的人格尊严,战俘存活率远高于德日营地,约为其八九倍。例外的是德军战俘,因法国人对德军迅速占领巴黎的痛恨,德俘遭受的待遇极其严厉,许多被直接枪毙,或被派往前线执行高风险的排雷任务,几乎无生存保障。
总体来看,意大利和法国对战俘较为宽容,是欧洲境内战俘存活率最高的国家。相比之下,美英两国的战俘营管理更显资本主义色彩,强调“人尽其用”,强制战俘从事繁重劳动。
美英战俘营的战俘都会获得工牌和工号,每天通过体力劳动换取工签,只有持有工签者才能领取补给。这种制度解决了太平洋战场的劳动力不足问题,许多美军士兵不愿干的苦活,全交给战俘干。英军对战俘劳动力的利用没有美军那么严苛,既是出于绅士风度,也因英军主要参与空战,工事建设需求较少。
为了保证劳动力供应,美英都曾明令禁止基层士兵随意虐待战俘,但依然有部分美军个别人“顶风作案”,对日俘施加折磨。特别是在日军对美军战俘的残酷行径被广泛知晓后,美军士兵对日军战俘的敌意更加强烈,经常趁机拳打脚踢。
此外,美军战俘营中的医护人员有时故意拖延对受伤日俘的治疗,导致伤口感染甚至死亡。但总体来看,美军对日军战俘的虐待未达到极端,甚至还给予部分著名日军将领如大场荣、舩坂弘荣誉称号,以示宽容。
与美英不同,澳大利亚对待日军战俘则毫无顾忌,甚至在表面功夫上都不做掩饰。澳军士兵铭记达尔文港轰炸和新几内亚战役的惨痛教训,日军战俘在澳大利亚营地通常先遭受鞭打、苦役、缺衣少食,奄奄一息时更被直接枪决,报复心切,手段极其严厉。
同样,苏军对日军战俘的待遇也极为严苛,仅次于对德军战俘的残忍。苏军的战俘政策强调“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因德国和日本给苏联带来了深重苦难,战俘营内对这两国俘虏的虐待屡见不鲜。苏军也强制德日战俘从事劳动,但对日军战俘的折磨远比德军战俘严重,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日军战俘被关押在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的极寒环境下,条件极其恶劣。
许多日军战俘在苏军的虐待和严寒中挣扎,最终没能挺过严冬的寒风。死去的日军战俘尸体甚至未获妥善安葬,直接被当作锅炉燃料焚烧,达到了“挫骨扬灰”的残酷境地。
综观二战各国对战俘的态度,我国对战俘的待遇无疑是最为宽厚的。无论是国军还是我军,都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以高度人道的方式处理战俘问题。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俘获的日军被集中管理,并进行思想改造教育。延安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日军战俘教育学校。
通过系统的思想洗礼,许多日军战俘觉醒,不再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部分人还加入抗战队伍,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军采取不虐待战俘、积极感化的政策,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也兼顾了现实需求。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效果显著,后期日本部队抵抗意志显著下降,主动投降的现象频频出现,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
发布于:天津市三亚股票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